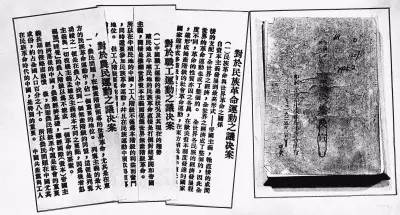長期以來,“農村包圍城市”被認為是中共取得革命勝利的重要原因,但農民是怎樣被發動起來的,歷來眾說紛紜,《邊區的革命》厘清了許多流行的謬誤。
國共產黨與工人階級要領導中國革命至于成功,必須盡可能地、系統地鼓動并組織各地農民逐漸從事經濟的和政治的爭斗。”在中共“四大”《對于農民運動之議決案》中,對農民運動給予高度重視。長期以來,“農村包圍城市”被認為是中共取得革命勝利的重要原因,近年來,學界有了不同看法。
首先,傳統中國農村土地分配相對均衡,貧富差距有限,在許多地區,即使“打土豪”,農民受惠亦不多,那么,如何才能將他們發動起來?其次,農民階級有所謂“狹隘性、保守性、自私性和分散性”,并非先進生產力代表,就算發動起來,對整體政局走向影響作用有多大?其三,早在1926年,國民黨便提出“二五減租”(減租25%),1930年6月《土地法》草案中,規定地租額為收獲總量的37.5%,實惠甚多,為何沒贏得農民的支持?
『圖為1925年1月22日發表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和《對于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等文件。』
一些學者認為,由于中共給了農民們選舉權,充分調動了他們“千百年來被壓抑的創造力”,才“創造了奇跡”。
而美國學者胡素珊在《中國的內戰》中則認為:土改的最大作用,在于改變了傳統鄉村的社會結構,從而斬斷了國民黨與農村的聯系,使其無法從中獲得資源。胡在著作中羅列了大量史料與數據,但較少實證分析,易給人以“語焉不詳”“大而化之”之感,而岳謙厚先生這本《邊區的革命》恰好補足了這個遺憾,它以一種“新革命史”的視角和邏輯手法,通過對各種新史料的多重比對和縝密分析,使邊區革命進程中的各種主客觀因素能夠清晰地呈現出來,并形成一個大致可視的“全相”。
有實惠并非全部原因
1938年,梁漱溟在延安與毛澤東徹夜長談,爭執不休,雙方最大分歧在于:梁認為中國農村貧富差距不明顯,而毛認為中國農村階級分化嚴重。
梁在山東鄒平搞了7年“鄉村建設”,而毛亦在湖南等地農村深入調查,但山東較富庶,土地分配相對平均;湖南則地處軍閥戰爭前線,各方爭相收稅,土豪劣紳被重用,農民苦不堪言。
當時農村貧富差距究竟如何?因統計材料不完整,只能看個案。
據中南軍政委員會土改委員會1950年編印的《土地改革重要文獻與資料》,江西1949年前原白區地主、富農共占人口11.3%,占有土地44.6%;湖南1949年以前丘陵地區,地主、富農占人口9.2%,占有土地64.1%。
而據1873年統計資料,當時英國貴族擁有土地73.9%,而他們只占土地擁有者(并非農村全部人口)的1.4%,剩下98.6%人口,僅擁有26.1%的土地。
據山西省永濟縣吳村檔案估算,土改前該村家戶地權分配基尼系數為0.421,個人地權分配基尼系數為0.355;土改后家戶地權分配基尼系數為0.272、個人地權分配基尼系數為0.228。
貧富差距客觀存在,但是否達到激化的程度,還需推敲。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邊區農民是怎樣被發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