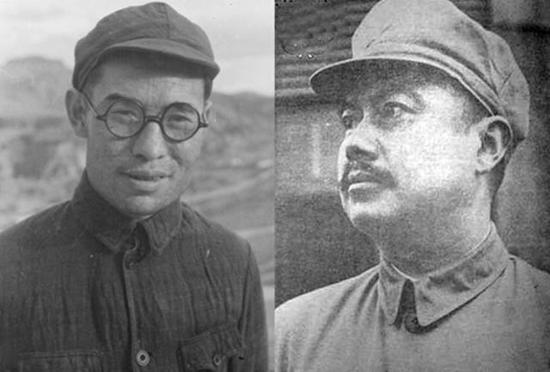1954年4月27日,“高饒事件”剛一定性,中共中央就通過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撤銷大區一級黨政機關,各大區行政委員會隨同各中央局、分局一并撤銷。新中國從此走上了中央高度集權的時代。
當時南方和西北多數省市任用的多是軍事干部,且是蘇區干部,而華北、東北多用的是黨政干部,且是白區干部,兩部分干部不僅有蘇區、白區之分,在文化程度上還相差甚多。這種分別不可避免地在中共干部當中造成某些隔閡與矛盾。這種隔閡與矛盾最突出地反映在了中央各部委一級干部的任用問題上面。這是因為,與過去農村蘇維埃政權時期的情況非常不同的是,新的全國性的中央政府的建立,不僅要考慮到絕大多數部委帶有很強的專業性質和文化水平的要求,而且還要考慮到當時因聯合政府的關系,一些重要部委的負責人,包括政府各部委成員中有相當數量文化知識程度很高的專家學者和社會名流,中央部委負責干部的任用難免也要考慮到文化水平的問題。
何況中央主管干部難免會找自己熟悉和用起來順手的干部來負責手下的部門,結果,在新成立的政務院部委,包括組織部和財經委員會等機構的負責人當中,除了李維漢、謝覺哉、滕代遠、李富春、王諍等少數人因長期在中央工作,或文化程度相對較好,或過去就有相當的專業工作經歷,故得以分任中央統戰部、內政部、鐵道部、重工業部、郵電部的部長、副部長外,其他多數部委的負責干部都選用了非軍隊系統的干部,且多用的是白區干部。這種情況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相當一批軍隊干部和蘇區干部的不滿。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白區正確路線代表的劉少奇,大力提攜重用經他營救出獄并曾長期在他手下工作的一些干部,如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劉瀾濤、廖魯言、胡錫奎等人,自然就成了眾矢之的。有“譚大炮”之稱的譚震林就曾直截了當地向毛澤東表示過對這種情況的強烈不滿。林彪也在背后有所謂“現在白區黨控制著中央的權力,很危險”的說法。不難了解,“高饒事件”的發生,正是這樣一種背景下促成的。
毛澤東作為蘇區正確路線的代表,自然也不能不受到此種情緒的影響。他在高崗到京后的言談話語間所透露出來的對劉少奇的不滿,在相當程度上就反映出他這時也并非不受影響。但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他不能不公開表現出中立的態度。在接見各大區負責人時,他一方面告訴大家:“譚震林對我說,中央有兩個司令部,白區黨的人掌握著黨權(組織、人事部門)、政權(政法部門)和財權(財經部門);另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大權旁落,這很危險,應該把權奪回來。”一方面解釋說:“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我已經批評了譚震林,不能說什么‘白區黨’、‘蘇區黨’。只有一個中國共產黨,一個司令部,就是黨中央。”而事實上,從他這時采取各種措施分散政府部門的權力,強化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接連發布《關于加強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對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等文件,規定政府各部門黨組直接受中共中央領導,以及通過財經會議及組織會議批評薄一波及安子文等等的做法,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并非對此毫無戒心與防范。當然,他這時尚不認為事情已經到了譚震林、林彪等人所說的那種地步。
戰爭條件下被無限放大的敵情意識,建國初期在各地反映出來的針對地下黨及本地干部缺乏信任的態度,嚴格說來應當是解放軍大舉渡江南下之后才突顯出來的。
據身為南京地下黨干部的穆廣仁回憶,1949年5月,南京剛剛占領不久,新成立的南京市委就得到了關于南京地下黨組織嚴重不純的情報。據此,南京市委上報中共華東局,一方面提出應馬上進行組織整頓,一方面請示對這些在解放南京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同時政治背景又極為復雜的南京地下黨干部應如何安排適當工作。中共華東局不能自作主張,故經曾作過中央社會部部長的第二副書記康生上報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隨即下達指示,除同意馬上進行整黨以外,并提出具體辦法為:“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中共建政后是如何“削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