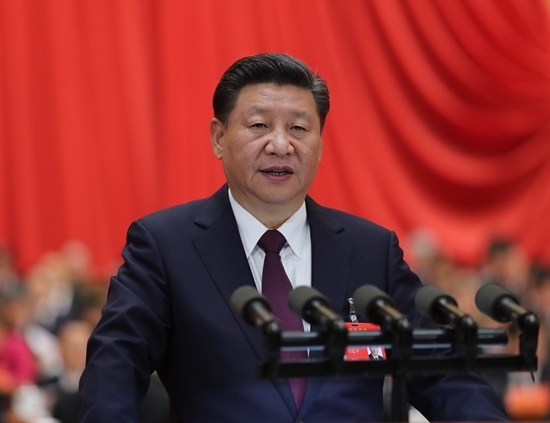[導讀]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新時代”的一個重大標志,是對當前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從過去“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發展”論斷的背后,既包含政治經濟學分析,也包含社會結構分析;既指出了中國發展正走向新階段,也指出未來發展將面臨更復雜的挑戰。
2016年,修遠基金會聯合各學科學者圍繞新時代、新周期開展研討,撰寫了《探索中國發展的新周期》的研究報告。今天,我們重新編發這份報告,期待與讀者一起,更好地理解和思考 “新時代”命題,以及其背后涉及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
報告對“新周期”討論直指“新時代”命題,包括三個層次:一是新的全球化形勢:中國的成長以及全球生產鏈條的復雜變遷使得簡單地“外向型經濟”模式難以為繼,未來中國的發展,不僅需要聚焦內部驅動力(創新經濟與轉型升級),還需要探索中國引領的區域協調發展(一帶一路與全球治理)。二是新的社會結構:目前的中國社會,正在被市場化、工業化進程重新定義,如何在高度復雜的社會結構中保持社會發展必要的流動性,可能是我們正在面臨的重大挑戰。三是新的治理邏輯:從政治形勢看,內外關系和社會領域的復雜變化,最終集中體現為對中國共產黨的治理能力和政治運行邏輯提出的新挑戰。更進一步說,新的全球化形勢、新的社會結構與新的治理邏輯,不僅僅是中國面臨的問題,也是處于社會撕裂、貧富分化、代表制失靈的世界各國普遍面臨的難題。這恰恰是“新時代”的時代性所在,而更好地解決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也成為“新時代”的普遍性歷史命題。
▍引言
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推動的政治、經濟改革戰略,開啟了中國特有的政經周期,伴隨反腐整風、吏治刷新、經濟結構調整、軍隊改革等一系列大手筆舉措,意識形態領域及社會輿論呈現出劇烈分化的態勢。人們對未來充滿期待,但對新的政經周期背后的歷史邏輯卻聚訟紛紜。有人懷疑這是否還是“100年不動搖”思想路線的繼續?繼經濟改革、社會改革之后應有普世主義的政治改革的歷史邏輯能否得到遵循?有人則由于30年發展帶來的社會分化、倫理失序、環境惡化,而干脆主張重返共和國第一個30年。
實際上,上述種種爭論可能都已經脫離了當下的實際:一方面,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以來,30年改革開放所依循的搭歐美世界經濟便車的模式已經難以延續,作為后發國家效仿對象的代議制民主及其政黨憲政制度也大面積失靈,曾經的“政經改革模板”都不同程度地失效;另一方面,經過3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中國的社會結構也發生劇烈變動,以農民工、城市白領、企業家為主體的新階級正不斷生成,傳統的工農社會正不斷重組,政府治理的對象已從農耕時代的靜態社會,加速轉變為高度流動的動態社會,人們的思想意識也已從傳統的集體主義轉向權利意識突出的個人主義,因此,重返前30年的老路也已經不具可能性。
以上種種明顯的經濟、政治、社會變動趨勢,均提示人們,在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前方,隱約呈現出一些新的基礎性的規律,仿佛出現了新的周期——如果說毛澤東時代是共和國的第一個周期,鄧小平時代是共和國的第二個周期,那么十八大以來的中國,是否正在步向一個新的周期?
我們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期待和想象,必須建立在這些基礎性條件之上,必須建立在對可能存在的新周期的深刻理解之上。否則,一切的呼吁都只是政治幻想。
本報告的目的,即在于討論自十八大以來新的政經周期背后的歷史邏輯,揭示內在于當下中國種種爭議不斷的政治經濟改革的深層規律,從而使人們的認識和行動更加自覺,更加能動地導向未來。
▍一、新的內外關系格局
1.全球化變局與中國發展路線的調整
最近幾年,中國經濟開始遭遇較大困難,經濟增速不斷下滑,結構性矛盾凸顯,中國開始告別已經延續了30余年的高速發展期,步入“新常態”。為了更好地理解“新常態”、理解當下的困境,我們有必要追溯過去一輪經濟增長的歷史條件,并在此基礎上,分析經濟環境發生深刻變遷的原因。
中國過去30余年的高速增長,開始于1970年代末。中國在1970年代末進行的改革開放,將中國經濟融入世界市場,既帶來了中國經濟的大發展,也將西方帶出了1970年代中期的“滯脹危機”,帶動了全球經濟走向新一輪的繁榮。
從表面上看,“滯脹”問題源于1973年的石油危機,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在已有的空間格局之下,資本的流動性已經到達頂點,沒有了價值洼地,生產鏈條中不同區域內生產資料價格趨于一致,持續盈利不再可能。為了走出1970年代滯脹危機,西方各國也進行了一些主動調整,通過市場化改革、通過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如里根和撒切爾改革)重新理順了資源配置體系,再度激發了經濟活力。
但是,這種改革只是存量的調整,真正的增量來源于資本活動空間的升級與擴大——在物理空間的廣度上和虛擬空間的深度上都能得到擴張。正像馬克思為我們揭示的,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區別于農業文明時代的核心特征,是可以進行擴大再生產。擴大再生產,要求資源和市場可以不斷開拓,由此資本才能無限增值。開拓資源和市場,就是開拓新空間,地理大發現、技術革命,都是在不同層面開辟新空間。
從1970年代末開始,一方面,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成為新的空間和價值洼地,融入全球市場體系之中,而接下來的80、90年代,蘇東社會主義體系瓦解并被納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另一方面,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技術變遷,帶來了對原有空間的深化利用,開辟了虛擬領域擴充資本的活動空間。
這也正如馬克斯· 韋伯(Max Weber)、費爾南· 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喬萬尼· 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到大衛· 哈維(David Harvey)等資本主義的追蹤者與研究者向我們揭示的:隨著資本量的增大,資本所需的空間也需不斷擴大,需要從一個競爭加劇的舊空間,跳躍至一個可以進行新一輪物質擴張的更大規模、更大范圍的新空間。
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加入,在更大的范圍和更深的層次上推進了生產環節的全球分布,意味著全球生產體系的“升級擴張”。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利用其最具競爭力的優勢——勞動力的高素質與低成本,降低了全球生產鏈條的生產成本,進而使自身成為世界工廠,使中國的產品走向世界,獲得了巨額的貿易收益,而發達國家也享受了中國低成本商品的紅利,中國與西方相互需要,各取所需。
然而,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這一輪全球經濟增長的長周期結束了。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產生的持續性不利影響,已經超出多數人的預期,經濟復蘇面臨重重困難,全球性的貿易與生產規模處于持續性的下降軌道。
例如,衡量經濟發展的關鍵指標之一——勞動生產率持續性下降: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從1999年到2006年,全球勞動生產率年平均增速為2.6%,2014年這一數值下降至2.1%。美國作為發達經濟體的代表,其勞動生產率也持續下降:2008年至2015年,美國年度勞動生產率平均增幅約為1.5%,不到上一次經濟繁榮期(1995?2003)年均增幅(3.5%)的一半。而中國的勞動生產率的增幅,也從2010年前后10%左右的年均增幅持續下降至2015年的7%左右。
除了這些具體經濟數據的下滑,金融危機的持續性影響,還進一步表現為世界經濟與政治治理體系出現嚴重困難。全球化秩序的三個支點——以聯合國集體安全機制為基礎的國際政治秩序、以美元信用為中心的世界金融體系、以WTO為基礎的自由貿易體制——都受到沖擊和挑戰。
對于美國、歐洲而言,一方面,因自由貿易對其不再有利,它們不斷推出貿易保護政策;另一方面,它們也逐漸以TTP、TTIP等區域性經濟政治設置,從全球化逐漸退后到區域整合,以此隔絕風險、整合區域市場,為將來更嚴酷的競爭積蓄力量。WTO體系因此受到挑戰。
與此同時,全球金融動蕩使得國際政治經濟的薄弱環節更易發生混亂。中東、非洲、拉美這些地區當前出現的社會危機和區域戰爭導致的難民等問題,又會向歐美地區擴散。聯合國等傳統國際政治協調機制,在這樣的場景面前顯然已無力應付。而為了應對危機,美國采取的量化寬松政策及其退出,導致國際資本的頻繁流動,不斷孕育新的金融風險,暴露了國際金融秩序的失序危機。
這一系列問題的出現,在更深層次上,意味著過去30余年全球經濟持續高歌猛進式的增長,已經走到盡頭;持續30余年的狂飆突進的資本全球化歷程,也已進入深度調整期,區域一體化、區域整合,這個原本就潛在于全球化進程中的線索,將逐步走向前臺,成為今后一段時間內的主題——在空間的廣度無法增長的情況下,需要轉向對已有空間縱深化的利用與整合。
從全球化向區域化的轉向,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無論是外部需求不足帶來的國際貿易動力不足,還是國際格局的整體變化,都可能導致中國長期發展道路面臨深刻挑戰。如果說,過去30余年改革開放的大背景是融入全球市場,而在全球化步入深度調整期的當下,我們已經無法簡單延續過去以大規模廉價商品輸出帶動經濟增長的粗放經濟模式。在世界市場相對衰退的背景下,我們需要根據歷史趨勢變化重新定位行動的基本邏輯,需要更多地從內部尋找經濟發展的動力。
2.中國經濟的內生需求: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
進入2012年以后,在經濟增速下滑的同時,中國經濟的一些新跡象也開始涌現:
在商業環境領域,以互聯網等信息技術為依托,商業模式創新在中國不斷出現,電商和快遞行業高速發展,出現了類似于淘寶網銷售額過萬億這樣具有象征意義的事件,出現了以智能手機應用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空間,也出現了類似于小米、滴滴出行、大疆無人機這樣的新興明星企業;
在工業技術領域,以裝備制造為中心,中國企業的技術突破大規模出現,高鐵成為中國制造的新名片,大型客機制造業走向正軌,超級計算機不斷推陳出新,還出現了華為這樣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世界級高科技企業;
在消費市場領域,中國社會財富積累已經到了一定的規模,對自身生活品質有著更高要求的新一代市民、新生代農民規模超過數億,消費能力驚人。伴隨著新一代消費主體對商品和服務質量要求的升級換代,中國出現了汽車銷售規模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這樣的象征性事件,也出現了電商行業對傳統農村市場的進軍與開發。
與此同時,政府和企業的投資能力也在不斷增長,跨國收購成為趨勢,如美的收購庫卡機器人,中國種業收購瑞士先正達集團等。
所有的這些新跡象,表明了中國經濟雖然遭遇到暫時性困難,但我們內部的一些創新性要素和能力,正在快速成長之中。
在過去30余年全球化擴張的大周期中,中國積累了龐大的經濟規模和巨量的社會資本,進一步完善了改革開放前30年已經初步建立起來的工業化體系,也進一步開闊了內部的經濟空間。在推行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中國涌現了多元性的經濟主體,并進一步激活了市場要素,使得市場體系出現了向更高階段演化的趨勢。正是這些活躍的多元經濟主體以及其他活躍的經濟要素,讓中國經濟至今仍然具備突出的活躍度,并由此形成了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的基礎,構筑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內部驅動力和經濟自主性。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并不是簡單地以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或以新的產業代替舊的產業,產業升級的實質含義是產業向較高生產率和較高附加值的經濟活動轉移,其背后是工業系統的演化發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轉型升級與創新發展必須建立在已有的相對完善的工業基礎之上。
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具有完整的工業體系。當下,中國的工業系統非常完備,既有以勞動力密集型為代表的制造行業,也有資本和資源密集型為基礎的重工業,還具有一定程度的技術密集型先進裝備制造業。完整的產業鏈既是維持經濟發展和保證人民就業的基礎,也是我們推動“轉型升級”與“創新發展”的前提。在全球化條件下,雖然出現了歐美的中低端行業外移的現象,但依托于大型跨國集團的強大生產組織能力和金融、軍事、技術霸權,歐美的高端行業依然可以實現對中低端行業間接但有效的控制。
對于中國而言,我們顯然還不具備此種去地域化的產業控制能力,如果盲目追求高端行業而忽視中端、低端的基礎產業,無異于緣木求魚。而且,在激烈的市場競爭條件下,高端行業的先在者——歐美跨國企業,顯然不會樂見出現具有威脅的后來者,自然會以強大而完善的技術壁壘、知識產權壁壘來限制自身技術的外泄,因此,中國的高端突破,更多地必須建立在提升低端和中端的基礎上,自主性地實現。如果說過去30年,我們依靠的是大規模、廉價的制造商品靠量取勝來獲得市場空間,今天,在國際市場空間的廣度相對下降的背景下,我們需要探索對國內生產、市場空間深度的挖掘,告別舊有的粗放式“量”的擴張模式,探索從量變向質變的轉移。
當前,為了順利地推進“轉型升級”、“創新發展”,為了更好地實現工業體系的擴展與演化,為了給各類企業發展提供更大的空間,我們需要比當下更大的市場空間和行動舞臺。正是在這樣一種內生力量的推動下,2013年以來,中央決策層大力倡導“一帶一路”、“亞投行”等戰略,推動中國自身的區域化布局:將中國與周邊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規劃,進行經濟空間的深度整合和開發,實現經濟網絡在更大范圍內的生長。
目前,中國處于世界經濟結構的節點之上,掌握著生產領域的結構性權力——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和大規模的資本持有量,不僅連接作為資源提供者的發展中國家,也連接作為主要消費者的發達國家。如果中國能從與周邊國家的交往合作中找到既促進他國發展也有利于我們發展的分工結構,就意味著可以打造出區域共同利益,形成區域共同體。中國也將借由推進區域一體化的契機,來學習和參與全球治理。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如何理解十九大提出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