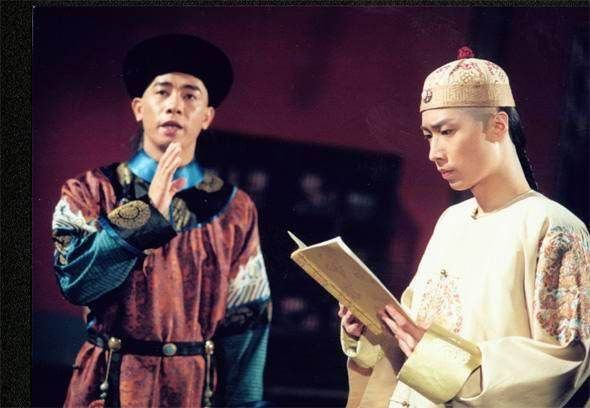賦稅制度的性質(zhì)對于政治形態(tài)及其演進(jìn)方向無疑具有重大的影響,比如1215年英國《大憲章》的誕生;1275年前后因英國地方貴族反對英王亨利三世的過度征稅而在牛津召開諮議會,遂使“議會”這種政治體制得以正規(guī)運(yùn)作;這時王室為了征稅而要求有各郡的民選代表參加議會,由此無平民代表即可召開議會的時代于1325年最終結(jié)束;直接起因于國王征稅而與國會或殖民地國民發(fā)生沖突的英國“光榮革命”和美國獨(dú)立戰(zhàn)爭等等,由這些事例我們看到:憲政制度從醞釀到建立漫長過程中這一系列關(guān)鍵的進(jìn)步,都是以稅額、稅制為博弈焦點(diǎn)才得以推動的。
然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對于皇權(quán)制度下的中國來說,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之間任何這類以制稅和財政監(jiān)督為焦點(diǎn)的博弈,始終就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更何況以此為支點(diǎn)而開啟整個政治和經(jīng)濟(jì)制度走出中世紀(jì)的進(jìn)程!
那么,中西道路和命運(yùn)之間這種巨大差異究竟是如何產(chǎn)生的?這種差異的深層制度原因是什么?這種制度原因又是遵從什么規(guī)律而貫穿了長久的歷史進(jìn)程、并且對社會發(fā)展方向產(chǎn)生著重大的影響?這些問題是本文希望能夠初步說明的。
“編戶齊民”的法理基礎(chǔ)
要說明中國皇權(quán)社會中賦役制度的性質(zhì),首先需要了解賦稅勞役的供給與征用雙方是處于一種什么樣的關(guān)系當(dāng)中,尤其需要了解這種關(guān)系是由什么樣的法理和法權(quán)制度所決定的。
我們知道,春秋戰(zhàn)國以后,各國諸侯取代周天子而成為大部分土地的實(shí)際所有者,而諸侯王通過“授田”將土地分給農(nóng)民耕種,同時將負(fù)擔(dān)徭役賦稅的責(zé)任一并強(qiáng)制性地“授”予農(nóng)民。這種王權(quán)統(tǒng)治之下的土地和人身關(guān)系,在秦漢以后歷時兩千余年未有根本變革,成為了作為皇權(quán)國家基礎(chǔ)的“編戶齊民”制度。對于這個制度的性質(zhì),需要特別注意兩點(diǎn):
一,在皇權(quán)統(tǒng)治之下,百姓沒有脫離“編民”制度而成為自由人的權(quán)利,他們?nèi)绻麍D逃離“編戶”,那就是嚴(yán)重的犯罪,官府必須對他及其家人施以嚴(yán)厲的懲處;即使是在皇權(quán)衰微時民口脫離國家編戶而成為豪強(qiáng)的“蔭戶”,改變的也只是依附對象而不是依附關(guān)系;由此,廣大國民、特別是農(nóng)民并不如以往常說的那樣,是自由民或自耕農(nóng)。因?yàn)樵谶@個制度的法權(quán)關(guān)系中,國民人身的存在價值,首先在于他是作為皇權(quán)統(tǒng)治基礎(chǔ)的“編戶齊民”制度中的一個分子,所以在中國傳統(tǒng)法律體系中,我們看到的就只有具體規(guī)定國民對皇權(quán)依附身份的“戶律”;此外,在皇權(quán)與國民的關(guān)系之中決不可能另有人身和人格“權(quán)利”的概念。
著名歷史學(xué)家王毓銓先生曾以農(nóng)民為例,說明中國皇權(quán)制度之下廣大國民身份的上述性質(zhì):
構(gòu)成古代中國封建歷史上的編戶齊民的主體的農(nóng)民(明代的“民戶”)的身分不可以說是“自由的”“獨(dú)立的”。他們的人身和其他編戶的人身一樣是屬于皇帝的。
……皇帝可以役其人身,稅其人身、遷移其人身,固著其人身。止要他身隸名籍,他就得為皇帝而生活而生產(chǎn)而供應(yīng)勞役;而不著籍又是違背帝王大法的。
……在古代中國的編戶齊民中,自由和獨(dú)立的事實(shí)是不存在的,可能連這兩個概念也沒有。……從周王說他受命于天為民之極起,一直到明清,沒有一個皇帝不是自許“奉天承運(yùn)”的。明朝的皇帝每于郊祀上報皇天牧養(yǎng)有成時,都是把全國的戶口簿籍(《賦役黃冊》)陳于祭臺之下,表示上天賜予他的對人民土地的所有權(quán)。有意義的是事經(jīng)兩三千年,在十七世紀(jì)以前,沒見有人對皇帝的這種權(quán)力提出質(zhì)問,更沒有人討論過編戶齊民為什么或是否應(yīng)該接受這種權(quán)力的支配。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人的權(quán)利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因?yàn)槭聦?shí)上它不存在。
他又詳細(xì)地說明這樣“身份”的國民何以必須對皇權(quán)承擔(dān)奴役性的勞役和貢賦:
朝廷有多少種勞役,就僉撥多少類人戶去承當(dāng)。種田的有民戶,當(dāng)兵的有軍戶,供造作的有匠戶,辦納鹽課的有灶戶(鹽戶)。這四大戶役,盡人皆知。另外還有陰陽戶、醫(yī)戶、儒戶、樂戶、陵戶、廟戶、壇戶、酒戶、醋戶、面戶、菜戶、鋪戶、水戶等等,總共不下五六十種,供應(yīng)不同的需用,或物或力。……一類役戶有一類役戶的籍(冊籍)。于是就有了與多少種戶役相應(yīng)類別的籍。如民籍、軍籍、匠籍、灶(鹽)籍等等。戶帖上具填明白。民籍、灶籍隸戶部、軍籍隸兵部、匠籍隸工部、鋪戶籍隸禮部等等,專一聽從該部差遣,如奴仆。
為什么編戶民服侍帝王如奴仆呢?因?yàn)檫@是他們的“本分”。(明)太祖皇帝說:“為吾民者,當(dāng)知其分。田賦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臣僚也都異口同聲地說:“為王之民,執(zhí)王之役,分也。”“分”,也叫“本分”。編戶民的本分就是納糧當(dāng)差。“說與百姓每(們),各守本分,納糧當(dāng)差不要誤了”。每月初一日皇帝下的《宣諭》就是這么教訓(xùn)老百姓的。
明白這種法權(quán)制度之下國民人身權(quán)利的性質(zhì),對于我們理解中國社會中的眾多問題都有重要意義。
第二,與上述“人身權(quán)利”的性質(zhì)相一致的,是關(guān)于國民財產(chǎn)權(quán)的法理。其核心是:普天之下一切財富在源頭上都是屬于帝王所有,而卑微的子民們能夠擁有財產(chǎn),全是出于圣德齊天的帝王之恩庇與賜福。所以“編戶小民雖然占有一小塊土地,甚至還可以進(jìn)行買賣,但在觀念上土地最高所有權(quán)一直屬于皇帝,誠如唐代陸贄所說:‘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nóng)人之所為。’當(dāng)編戶小農(nóng)人身還是被占有的時候,他們的土地占有權(quán)的意義是不會超過他們的人身的意義的。”3對于皇權(quán)之下國民財產(chǎn)權(quán)的這種性質(zhì),在唐代柳宗元代表長安縣百姓呈給皇帝的一份奏表中表述得很清楚:
(陛下)盛德廣大,玄化益被。加以休徵咸集,福應(yīng)具臻,至于今歲,紛綸尤盛。風(fēng)雨必順,生長以時,五稼盡登,萬方皆稔。……臣等得生于邦甸,幸遇圣明,身體發(fā)膚,盡歸于圣育;衣服飲食,悉自于皇恩!
因?yàn)槭駬碛胸敭a(chǎn)完全是他們有幸居身于“皇恩”之下的結(jié)果,所以那種不知恩養(yǎng)、不圖以承擔(dān)賦役而報答皇帝恩德者,乃是犯下了人神共憤的大罪;于是他的財產(chǎn)不僅絲毫不具備法律上的不可侵犯性,而且注定將不為其所有2——可見在國民個人財產(chǎn)所有權(quán)之上,還有著一重最終、也是最為神圣的所有者,這就是帝王。
明白了上面的道理,也就立刻可以知道為什么在中國傳統(tǒng)法律制度中,根本不可能如羅馬法對“所有權(quán)”的定義那樣,強(qiáng)調(diào)所有者享有絕對的產(chǎn)權(quán);更不可能如羅馬法系那樣以“財產(chǎn)法”為核心而建構(gòu)起完整的私法體系、并使私法與公法相分立。而中國皇權(quán)制度此種法理派生出的,當(dāng)然是迥異于西方的賦稅制度。
順便說一句,王毓銓先生曾擔(dān)心因?yàn)椤吧钤诮裉斓娜瞬皇至私夤糯纳詈椭贫取倍y以理解中國賦役制度的上述性質(zhì)。然而如果我們不是有意無意地去忽視中國社會的基本現(xiàn)實(shí),則這種隔膜其實(shí)并不存在。因?yàn)橹钡浆F(xiàn)在,中國廣大農(nóng)民所承擔(dān)的賦役制度(以及其背后的農(nóng)民身份和戶籍制度)依然鮮明地留有“編戶齊民”的特征;李昌平在他那篇引起國人強(qiáng)烈反響的哭訴信中所描述的當(dāng)今情況是:
80%的農(nóng)民虧本,農(nóng)民不論種不種田都必須繳納人頭費(fèi)、宅基費(fèi)、自留地費(fèi),喪失勞動力的80歲的老爺爺老奶奶和剛剛出生的嬰兒也一視同仁交幾百元錢的人頭負(fù)擔(dān)。由于種田虧本,田無人種,負(fù)擔(dān)只有往人頭上加,有的村人頭負(fù)擔(dān)高過500多元/人。我經(jīng)常碰到老人拉著我的手痛哭流淚盼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上學(xué)的悲傷場面。我除了失聲痛哭外,無法表達(dá)我的心情。痛苦與無奈一切盡在哭泣中。
而因?yàn)樯矸葜贫群唾x役制度性質(zhì)并未根本改變,所以由此而衍生的從古至今無數(shù)悲劇,往往在形式細(xì)節(jié)上都十分相似,比如李昌平所說經(jīng)常有老人“痛哭流涕盼早死”以求免除家人稅役,這種萬無出路的絕境其實(shí)早有先例——北宋英宗時財稅官(三司使)韓絳就提到當(dāng)時酷役制度之下的慘目例子:“東京民有父子二丁將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當(dāng)求死,使汝免于凍餒’,遂自縊而死。”2
中西稅賦制度的重大區(qū)別
對于中國皇權(quán)制度中賦稅制度的基本性質(zhì),韓愈的名言也許是最為扼要的說明:
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財貨,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
這話將賦役制度完全是皇權(quán)絕對統(tǒng)治其國民之工具的性質(zhì)闡述得非常直白。而人民通常更是直接以“皇糧”、“官課”、“王役”等等名詞,以直接以說明賦稅體制對皇權(quán)及其官僚制度利益的完全從屬——恰如百姓以“王法”、“官法”等名稱來概括中國法律制度的屬性5一樣。由此可以使我們直覺地感到,這種將“以事其上”作為根本目的的賦稅制度與憲政方向的賦稅制度之根本不同。
對于這種不同,王毓銓先生曾具體說明:
什么是近代的稅呢?
照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創(chuàng)始人亞當(dāng)·斯密(Adam Smith)的說法,近代的(即他當(dāng)時的)稅的征收有幾條基本原則,其中最重要的兩條是:第一,每個國家的公民應(yīng)該按照他在國家保護(hù)之下獲得的收入,繳納其一部分給政府,以支持政府;第二,每個人向國家繳納的稅額是一定的,但不是專斷的。亞當(dāng)·斯密列出的稅征原則是屬于近代資產(chǎn)階級代議制國家的,納稅的人是那個政府的公民。拿這原則和古代封建中國的稅收相較,便可發(fā)現(xiàn)兩者不同。古代封建中國的編戶民繳納的稅不一定是納稅的一部分,可能是他收入的多半部分甚至全部。其按照丁田(主要是田)所派征的物料,稅額雖原有規(guī)定,但可隨時改變,也可隨時增加,“節(jié)年多寡不同,(州縣)一如府帖應(yīng)納。”(海瑞:《淳安縣政事》),“大要取給公家而止”(嘉靖《徽州府志·歲供》)。“事出朝廷,無奈之何!”(海瑞,同上)……古代中國的稅不只是不一定的,而且是專斷的。……近代的土地稅不是役,而古代中國的封建田賦則是役,而且完全是役(王毅注:即民戶因其對皇權(quán)的依附身份而必須承擔(dān)的服事性勞役)。近代的土地稅建立在土地私有制之上,古代封建中國沒有土地私有制,所以不可能產(chǎn)生近代性質(zhì)的土地稅。而且近代國家納稅者是公民,法律上是平等自由的,而古代中國的差稅繳納者則是具有封建的人身依附關(guān)系而隸屬于帝王的編戶齊民。
聯(lián)系上節(jié)所敘述的人身與財產(chǎn)權(quán)利的問題,則可以知道中國的賦稅和勞役制度,仍然不過是皇權(quán)對其“子民”天然地具有無限統(tǒng)治威權(quán)的具體表現(xiàn)之一。所以,作為天命神授統(tǒng)治威權(quán)的具體化,帝王的制稅權(quán)、制役權(quán)、增稅權(quán)、甚至是惡稅權(quán)等等,也就與“編戶齊民”制度一樣,是從每一個“子民”出生落地時開始就籠蓋在他們頭上的,而絕不可能如真正的財產(chǎn)私有制度中那樣,僅是一種滌除了人身依附關(guān)系之后的財產(chǎn)所得稅。
中西制稅法理的上述根本不同,在經(jīng)濟(jì)制度形態(tài)上當(dāng)然有著廣泛深刻的表現(xiàn)。而近年顧鑾齋先生從事的“中西中古稅制比較研究”則對此做出了全面的分析,其中的一些結(jié)論如下:
一、稅權(quán)歸屬。中西中古稅權(quán)的歸屬存在重大差異。在中國,稅權(quán)歸于中央,并進(jìn)而歸屬皇帝;在西方則歸于某一權(quán)力集體,例如英國,這一權(quán)力集體先后經(jīng)歷了御前會議、貴族大會議、國會三種形式。隨著中古社會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的發(fā)展,稅權(quán)問題在西方得到了比較理想的解決,逐漸形成了“先補(bǔ)償,后供給”的原則,即在國王向納稅人提出征稅要求的同時,納稅人據(jù)此也向國王提出包括政治權(quán)力、經(jīng)濟(jì)利益、司法審判等方面的要求……
二、稅收理論。中西封建社會具有不同的稅收理論。這些理論之所以不同,與帝王、國家、政府三者間不同的結(jié)合形式密切相關(guān)。在中國,皇帝、國家、政府三位一體,皇帝視國為家,視人為子,既代表政府,也代表國家。在西方,國王與政府雖結(jié)為一體,因而政府被稱為國王的“私人政府”,但國家是分立的,國王代表了政府,卻不能代表國家。所以,中國皇帝以中華大家庭家長的身份征稅,對稅款實(shí)施“強(qiáng)權(quán)征收”,并不征求納稅人的意見,當(dāng)然更談不上征得納稅人的同意。西方賦稅理論具有深厚的歷史基礎(chǔ)。這種理論在其形成過程中曾受多種因素制約,其中最重要的是特定的私有制形態(tài)、羅馬法和經(jīng)院學(xué)說。按照這一理論,對封建稅的征收乃是國王的特權(quán),我們稱為“特權(quán)征收”;對國稅的征收則須以稅款使用符合全國人民的利益為前提,即所謂“共同利益”。
四、賦稅收支。基于“家國一體”的建構(gòu)模式,中國中古稅收具有突出的強(qiáng)制性質(zhì),我們稱之為強(qiáng)權(quán)收入。而由于西方中古社會沒有形成強(qiáng)固的宗法制和“國、民王有”觀念,且王權(quán)僅代表政府而難代表國家,西方稅收在中古前期主要依靠特權(quán)取得收入,后期主要依靠協(xié)商取得收入,所以我們把前、后期分別稱為特權(quán)收入和協(xié)議收入。強(qiáng)權(quán)收入是指政府主要通過國家強(qiáng)權(quán)和高壓政策取得收入,它具有兩個顯著特點(diǎn):一是隨意性;二是專斷性。特權(quán)收入是指依據(jù)封建特權(quán)取得收入,它也具有兩方面特點(diǎn),一是收入項目一般以傳統(tǒng)或慣例作為依據(jù);二是排它性、壟斷性。協(xié)議收入是指國王通過與納稅人或納稅人代表組成的集體協(xié)商而獲得收入,其特點(diǎn)是國王或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尊重納稅人的財產(chǎn)所有權(quán),取得收入的過程體現(xiàn)出一定的民主性。
……
七、中古稅制與政體形式。中國由于在中古社會定型時期已經(jīng)形成了財稅專權(quán)體制,專制政體自始即獲得了堅實(shí)的財政基礎(chǔ)。在我們看來,財政專權(quán)和由這一專權(quán)形成的財政基礎(chǔ),是專制政體不斷加強(qiáng)并于明清達(dá)到登峰造極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國中古社會長期延續(xù)的基本原因。在西方,由于某一權(quán)力集體特別是議會執(zhí)掌稅權(quán),中古社會一直沒有形成專制政體而主要采取等級君主制的形式。在傳統(tǒng)社會向近代社會的轉(zhuǎn)型中,由于英國議會牢固地控制著稅權(quán),王權(quán)雖有一定加強(qiáng),政體形式卻無實(shí)質(zhì)性變化。
從中國皇權(quán)稅制“強(qiáng)權(quán)收入”特性與歐洲“議會執(zhí)掌稅權(quán)”、“協(xié)商取得收入”的分野中,我們當(dāng)然可以很強(qiáng)烈地感到兩種稅制以及他們后面的兩種政治制度的巨大差別,以及這種差別在各自社會發(fā)展方向上完全不同的導(dǎo)向作用。
轉(zhuǎn)載請注明:北緯40° » 中國古代的稅制改革為什么總是越改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