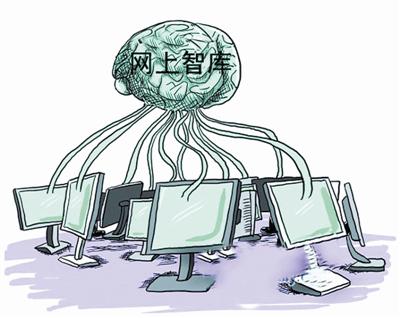核心提示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 預示著中國智庫發展迎來新的轉折點。在此戰略背景下,作為國防和安全領域問題研究的核心力量,軍事智庫的建設成為與之伴生的課題。而信息化大勢下,網上軍事智庫建設在資源聚合、輿論引導、研究成果推廣等方面具有先天優勢,因此成為中國特色新型軍事智庫建設的題中之義。
2015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要求2020年建成“一批具有較大影響力的高端智庫”,其中指出,軍隊系統重點教學科研單位先行開展高端智庫建設試點。
新型智庫建設勢在必行。然而,1月22日的日本《外交學者》則撰文指出,“在中國,具有較大影響力和國際知名度的高質量智庫缺乏,提供的高質量研究成果不夠多,資源配置不夠科學,領軍和杰出人才也匱乏。”無論現狀如何,我國軍事智庫的發展都需要解決大量的問題,而網上軍事智庫在資源配置及擴大影響力方面較實體智庫更為有利,因此,“實體+網絡”軍事智庫將是互聯網時代中國特色新型軍事智庫發展的內在要求。
發揮資源聚合效應
目前,我國軍事智庫主要分為三大類,即以軍事科學院、國防大學、國防科技大學等軍內科研機構及院校,中央和地方黨政軍事智庫等官方智庫,以及民間軍事智庫。同中國其他智庫一樣,很多軍事智庫是在上世紀50年代初按照蘇聯模式創建的,它們的研究大都是由從上至下的指令推動的,因此軍地間、智囊間、學科間互動交流不夠。
有專家指出,在實踐中,軍內專家通曉國家發展戰略的不多,地方智囊研究軍事戰略的也不精,軍地社科資源相對分散,制約了國家發展與安全政策制定的有機統一。
誠然,國家的發展與國防安全息息相關,這就要求提供決策參考的軍事智庫研究者既懂軍事兵情,又懂國事民情。但我軍從事理論研究的現役軍人,真正擔任過師旅以上主官或大區以上機關高級領導職務的為數不多,退役中高級干部參與軍事咨詢工作的制度機制并不健全。
作為思想產品的生產者,高端人才是智庫的第一要素。而中國智庫在人員分布及溝通交流上的孤立現象不僅導致大量重復性勞動,更是造成資源浪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教授王文提出“開放式智庫文化”,即以互聯網思維,構建政策開放討論和決策制定社會化的網絡平臺,促進決策者、研究者和公眾多方頻繁而有效的積極互動,強化一流智庫在公共政策制定層面的重要角色,尤其要獲得有智之士主動性、先見性的智力支持,而網上軍事智庫可為軍地各方人才的交流互動提供平臺。
官方軍事智庫師資實力雄厚、信息來源廣泛,而民間軍事智庫與社會接觸更多,觀點具有客觀、中立的優勢,因此,雙方信息的交流對于軍事智庫研究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有所裨益。不論是作為軍事智庫服務對象的政府決策者,還是處于政策末端的大眾,都更希望軍事智庫的研究成果基于客觀現實并滿足現實需求。然而,由于軍事系統的保密要求,軍事智庫研究人員和研究話題在公共平臺都有所限制。因此,網上軍事智庫為信息的溝通提供便利的同時,也要做好開放和保密的管理層面的技術設計。
引導軍事輿論走向
新媒體環境下,信息傳播速度快、范圍廣,也使得輿論掌控難度更大,而與之相應,運用新媒體進行輿論引導也更具時效和成效。在典型涉軍事件“棱鏡門”中,美國政府、政客、媒體紛紛以新媒體的力量,為該行徑辯護。事發第二天,美國國家安全局開通Twitter官方賬戶,當天發布信息47條,該賬號在個人介紹中改編富蘭克林的一句名言,稱“如果你愿意拿自由交換安全,我們會竭力保證你的安全”。
在網絡環境中,信息來源豐富,并可能被多重傳播,由此,堅定及時的主流聲音顯得尤為重要。經濟學中的“二八定律”在網絡輿論空間同樣適用:80%的聲音一般由20%的網民發出,表明在網絡中意見領袖的重要性。而且全媒體時代,網絡聚合效應明顯,易發生群體性傾向,對于較為敏感的軍事問題,智庫觀點往往較黨政機關的公關更容易為人接受。軍事智庫聚集了軍事領域最優秀的專家學者,智庫成員可充分利用新媒體工具發揮意見領袖的權威性。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中國國防報:網上軍事智庫乘勢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