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yuǎn)不可能出現(xiàn)不必調(diào)整就可保障長(zhǎng)久安全的政策,一種有利于國家生存的安全路線必須同時(shí)兼顧節(jié)制與靈活,就像俾斯麥所說的那樣,治國方略中永遠(yuǎn)不存在抽象的最優(yōu),因?yàn)椤罢问强赡苄缘乃囆g(shù),是可實(shí)現(xiàn)的藝術(shù)——是次優(yōu)的藝術(shù)”。
一般而言,歷史學(xué)家把俾斯麥在1890年的退休視為德意志帝國的歷史轉(zhuǎn)折點(diǎn)。從那一年起,德國拋棄了以聯(lián)俄為中心的“三皇同盟”,開始向范圍更廣的“世界政策”進(jìn)軍,與英國的傳統(tǒng)友好關(guān)系則因大海軍建設(shè)的興起而陷入對(duì)立。最終,正是與英俄兩國關(guān)系的惡化加快了德國走向大戰(zhàn)的步伐,并最終導(dǎo)致了第二帝國的崩潰。
然而,使柏林有能力追逐“陽光下的土地”、并在海陸兩個(gè)方向同時(shí)與英俄兩強(qiáng)對(duì)抗的經(jīng)濟(jì)和工業(yè)基礎(chǔ),恰恰是在俾斯麥任內(nèi)打下的。這就涉及到一個(gè)問題:為什么俾斯麥沒有像后來的威廉二世一樣變成海軍迷?從1871年到1890年,德國是如何在沒有一支強(qiáng)大海軍的情況下,持續(xù)強(qiáng)化自己的國力并確保外部安全的?
首先來看德國統(tǒng)一之際的歐洲格局。在拿破侖戰(zhàn)爭(zhēng)后的“不列顛治下的和平”(Pax of Britannia)時(shí)代,英法俄普奧五強(qiáng)在大陸上的力量分布趨于均衡,這種均衡使得各國更傾向于以協(xié)調(diào)而不是沖突的方式來解決利益分歧,歐洲也得以在1815年之后,保持總體和平超過半世紀(jì)之久。然而,1870-71年普魯士在對(duì)法戰(zhàn)爭(zhēng)中取得了意料之外的勝利,它在其他列強(qiáng)來得及作出反應(yīng)之前就完成了統(tǒng)一。現(xiàn)在,中歐核心區(qū)域突然出現(xiàn)了一個(gè)人口總量、經(jīng)濟(jì)潛力和軍事實(shí)力高達(dá)周邊其他國家兩倍的“巨型中等強(qiáng)國”,顛覆了多極格局,也造成了歐洲體系的重新洗牌。
作為新國家的締造者和德國外交路線的制訂人,俾斯麥窺見了統(tǒng)一帶來的震蕩:在五強(qiáng)勢(shì)力均衡的年代,各國更重視彼此的動(dòng)機(jī);但因?yàn)榈聡F(xiàn)在已經(jīng)擁有了高出周邊國家一截的工業(yè)能力和陸上軍力,其他國家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將是這種硬實(shí)力可能給自己造成的危害。無論德國怎樣韜光養(yǎng)晦、做出善意表態(tài),它都不可能回到1870年之前“悶聲大發(fā)財(cái)”的狀態(tài)了。而德國本身的地理位置相當(dāng)不利——它的世仇和主要安全威脅法國盤踞在臥榻之側(cè),英國和俄國兩個(gè)側(cè)翼大國則有機(jī)會(huì)從東西兩側(cè)包圍中歐,使柏林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境。個(gè)中情境,恰如俾斯麥早年的慨嘆:“世間堂皇之物……每每與墮落天使相仿:華麗但欠和平,計(jì)劃及努力卓越然不得成功,驕傲卻又憂郁。”
正因?yàn)榈聡臋?quán)勢(shì)基值是如此驚人、地理位置又極其敏感,俾斯麥從一開始就不把攫取歐陸霸主地位作為目標(biāo)。在1877年口述的一份重要文件《基辛根溫泉備忘錄》中,“鐵血宰相”提出了他的行動(dòng)依據(jù):與漫無目的的“稱霸”相比,德國更應(yīng)當(dāng)擔(dān)心自己“被包圍”。柏林現(xiàn)在的一舉一動(dòng)都受到其他國家高度關(guān)注,一旦被認(rèn)定威脅到了普遍安全,從北海到烏拉爾山都將是它的敵人。但除去法國與德國的仇恨難于化解外,德國和英奧俄這三國是存在利益交集的,只要在這三個(gè)國家中爭(zhēng)取到至少兩國的友誼,柏林在五強(qiáng)中就屬于多數(shù)派,即使爆發(fā)戰(zhàn)爭(zhēng)也不會(huì)吃虧。但英俄、俄奧甚至小一點(diǎn)的意大利之間本身也存在復(fù)雜的利益糾葛,德國很難把它們拉進(jìn)一個(gè)協(xié)調(diào)一致的陣線。有鑒于此,俾斯麥提出了一個(gè)概念——“誠實(shí)的經(jīng)紀(jì)人”(Honest Broker)。簡(jiǎn)單地說就是德國不為自己索取領(lǐng)土和安全利益,但熱心為其他國家充當(dāng)仲裁者和中間人,使這些國家對(duì)德國產(chǎn)生信任甚至依賴。這樣一來,歐洲任何大的領(lǐng)土變更或安全事務(wù)都需要德國參與協(xié)調(diào),那么以德國為敵的大國聯(lián)盟也就永遠(yuǎn)不可能出現(xiàn)了。
1890年之前的德國外交,或者說“俾斯麥體系”,就是根據(jù)這樣的理念建立起來的。它是一系列由精心編織的利益鏈構(gòu)成的網(wǎng)絡(luò):對(duì)奧匈,德國與之結(jié)盟、但約束其行動(dòng),使維也納不至于因自行其是而把柏林推向俄國的對(duì)立面;對(duì)俄國,俾斯麥?zhǔn)紫冉⒘艘粋€(gè)“善意”的德奧同盟,接著邀請(qǐng)俄國加入,這樣彼得堡就不再期待與法國結(jié)盟了。同時(shí),在涉及土耳其的“東方問題”上,俾斯麥暗中支持俄國與英國對(duì)立,以消弭兩個(gè)側(cè)翼大國步調(diào)一致包圍德國的機(jī)會(huì)。對(duì)法國,“鐵血宰相”慫恿其向非洲和亞洲發(fā)展,從而與英國的殖民利益產(chǎn)生沖突。對(duì)英國,柏林明確表態(tài)無意插足海外,同時(shí)在埃及事務(wù)和黑海海峽問題上協(xié)助英國牽制法俄,以換取倫敦的友誼。這樣一來,英俄奧三國皆有一定矛盾,它們需要德國的程度將大于它們互相需要的程度,于是德國成為大國事務(wù)中最有分量的中間人。它的國際形象被認(rèn)為是積極的,它的高速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和工業(yè)進(jìn)步也沒有被認(rèn)為威脅到了和平。
俾斯麥體系的基本假設(shè)在于:德國因?yàn)榈乩砦恢貌涣迹炔豢赡芩翢o忌憚地追求霸主地位——那將重蹈路易十四和拿破侖的覆轍——也不可能在沒有解決歐洲安全問題的情況下,突然跳到海外去建立某種“世界帝國”。在歐洲的相對(duì)優(yōu)勢(shì)是最可取、風(fēng)險(xiǎn)也最低的:當(dāng)時(shí)的世界體系基本以歐洲為中心,只要德國在歐洲的地位不可替代,它完全不必去新建一個(gè)有形的“世界帝國”就可以成為無形的第一等大國。
但俾斯麥體系也有缺點(diǎn):它是一種永恒的動(dòng)態(tài)平衡,需要極高水平的理解力才能加以操作。俾斯麥認(rèn)為,一方的強(qiáng)大導(dǎo)致另一方的恐懼,德國統(tǒng)一的完成必然帶來外部環(huán)境的惡化,這是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的。除了節(jié)制力量、根據(jù)形勢(shì)變化調(diào)整結(jié)盟關(guān)系外,德國并沒有更好的出路。換言之,柏林必須始終與不安為伴,不可能獲得絕對(duì)意義上的“解脫”,而大多數(shù)領(lǐng)導(dǎo)人是忍受不了這種狀態(tài)的。另外,“鐵血宰相”是一位古典政治家,在完成統(tǒng)一事業(yè)的絕大部分時(shí)間里,他只需要說服普王威廉一世和少數(shù)高級(jí)將領(lǐng),卻缺乏應(yīng)對(duì)民意及其代表的意愿和經(jīng)驗(yàn)。俾斯麥甚至有意識(shí)地把第二帝國的代議政體和憲法條款搞得簡(jiǎn)單化,方便自己完全靠一人的智慧把握國家大政。但進(jìn)入1880年代,新興工商業(yè)階層已經(jīng)成為一股強(qiáng)大的社會(huì)力量,他們要求效仿英法等國、攫取海外殖民地,并且在國會(huì)里控制了話語權(quán)。這個(gè)時(shí)候,仍在以1871年之前的經(jīng)驗(yàn)把握方向的俾斯麥有點(diǎn)招架不住了。
“鐵血宰相”對(duì)殖民地的觀感是比較負(fù)面的:首先,管理殖民地需要財(cái)力、人力、無力,向殖民地輸入商品、輸出資源的前提是投入成規(guī)模的征服和開發(fā)成本,且開發(fā)之后的回報(bào)率還尚未可知。目前,德國僅靠開發(fā)歐洲市場(chǎng)就可以獲得可觀的收益,對(duì)殖民地沒有需求。其次,維持和保衛(wèi)殖民地將增加德國與其他強(qiáng)國發(fā)生沖突的幾率,這會(huì)對(duì)在歐洲充當(dāng)“誠實(shí)的經(jīng)紀(jì)人”產(chǎn)生負(fù)面影響,而考慮到歐洲問題的中心地位,因?yàn)橹趁竦貭?zhēng)端影響核心利益是不值得的。但隨著公眾輿論的呼聲愈演愈烈,他決定改變思路:1884年,德國宣布將多哥蘭、喀麥隆和西南非洲置于自己的保護(hù)之下。第二年11月,“德國殖民協(xié)會(huì)”創(chuàng)始人卡爾·彼得斯登陸非洲東海岸,將總面積達(dá)14萬平方公里的坦噶尼喀殖民地收入本國政府囊中。太平洋方面,德國在1884-1888年先后獲得了新幾內(nèi)亞、俾斯麥群島、所羅門群島、布干維爾島和瑙魯,加上在非洲的收獲,總面積超過100萬平方公里。
需要指出的是,幾年后,當(dāng)威廉二世開始全面推進(jìn)“世界政策”、大張旗鼓地追逐殖民地和海外利益時(shí),他的實(shí)際收益不到這一時(shí)期的1/10。換言之,“一戰(zhàn)”爆發(fā)前德國擁有殖民地面積的90%,是俾斯麥在1880年代中期不到三年的時(shí)間里,以無心插柳的方式爭(zhēng)取到的。這樣的擴(kuò)張之所以沒有引起多少反彈和敵意,關(guān)鍵就在于它和作為主要目標(biāo)的歐陸戰(zhàn)略是相互配合的:德國開始殖民非洲的1883年,正值英法交惡、法德關(guān)系緩和,德國這時(shí)在英國占據(jù)優(yōu)勢(shì)的幾內(nèi)亞灣打進(jìn)一個(gè)釘子(喀麥隆),具有向法國示好的意味。兩年后法國內(nèi)閣更迭,俾斯麥馬上終止在非洲的動(dòng)作,轉(zhuǎn)而與英國修復(fù)關(guān)系。而德國在非洲和太平洋新開辟的殖民地,面積固然不小,但都小心地避開了英國最忌憚的埃及、印度等敏感區(qū)域。換言之,在增加海外領(lǐng)土面積的同時(shí),盡量避免在歐洲的“經(jīng)紀(jì)人”形象受損。
海軍發(fā)展是與殖民地開拓直接相關(guān)的一個(gè)問題,在這方面,俾斯麥依舊抱消極、但不絕對(duì)否定的態(tài)度。1873年,國會(huì)通過了獨(dú)立后第一個(gè)十年海軍發(fā)展計(jì)劃,旨在建成一支以巡洋艦、魚雷艇和岸防裝甲艦為核心的防御型艦隊(duì),保護(hù)德國在北海和波羅的海的利益。俾斯麥對(duì)這個(gè)方案持認(rèn)可態(tài)度,但始終反對(duì)過早建立英國式的大海軍。除去經(jīng)濟(jì)方面的考慮外,這依然是基于他對(duì)“絕對(duì)安全”觀念的否定——擁有最強(qiáng)陸軍的國家同時(shí)又在追求第一或第二強(qiáng)的海軍,這將使所有周邊國家感受到無可比擬的壓力,并在最壞結(jié)果到來前就聯(lián)合起來對(duì)其進(jìn)行制衡。而柏林不像英國那樣擁有超然世外的地理優(yōu)勢(shì),一旦發(fā)生沖突,法俄兩國立時(shí)就可自陸地侵入德國領(lǐng)土,結(jié)果將是一場(chǎng)災(zāi)難。
那么,德國要通過何種方式來保護(hù)自己的海外利益呢?如果未來戰(zhàn)爭(zhēng)發(fā)生在它和法俄之間,已有的巡洋艦和魚雷艇足夠?qū)橙说暮I辖煌?gòu)成威脅,而德國大可利用它和英國之間距離較近的優(yōu)勢(shì),以英國為中轉(zhuǎn)站和地理掩護(hù),繼續(xù)向大西洋派出商船。而如果戰(zhàn)爭(zhēng)是發(fā)生在德國和英國之間,它也可以聯(lián)絡(luò)在1856年《巴黎條約》(載入了航行自由原則)上簽字的其他二流海軍強(qiáng)國,構(gòu)建“武裝中立同盟”,像美國獨(dú)立戰(zhàn)爭(zhēng)期間其他歐洲國家抵制英國一樣對(duì)皇家海軍進(jìn)行牽制。至于“一勞永逸”地杜絕英國對(duì)德國海外利益的侵害,這根本不具備可操作性。
如果把威廉二世時(shí)代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與海權(quán)偏執(zhí)和俾斯麥的主張做一番對(duì)比,不難看出,它們恰恰違背了“鐵血宰相”最看重的兩大信條。首先,俾斯麥認(rèn)為:德國最切身的安全利益在歐洲內(nèi)部,只要能避免在歐洲形成針對(duì)柏林的制衡聯(lián)盟,德國的繁榮和強(qiáng)大就有保障,世界影響力更是可以不求自來。而威廉二世有一種簡(jiǎn)單粗暴的“中二病”心理,他認(rèn)為德國之所以不能在國際事務(wù)上為所欲為,關(guān)鍵就在于它只是一個(gè)歐洲強(qiáng)國,而沒有像英國那樣取得“世界強(qiáng)國”的地位;如果能在全球開拓出大片殖民地、并建立起規(guī)模驚人的遠(yuǎn)洋海軍,歐洲國家就不再具有反制德國的能力了,柏林卻可以為所欲為地懲戒任何杵逆者。但日后的事實(shí)證明,缺少了歐陸安全作為基礎(chǔ),“世界強(qiáng)國”不過是一張畫餅。法俄兩國的結(jié)合令德國的安全環(huán)境出現(xiàn)了根本性的惡化。
其次,俾斯麥認(rèn)為,不存在一種無條件的、絕對(duì)意義上的安全。在一個(gè)由若干大國組成的封閉系統(tǒng)里,一國安全指數(shù)上升過快勢(shì)必招來其他國家的恐懼,繼而促成制衡聯(lián)盟。有鑒于此,必須明辨關(guān)系國祚存亡的核心利益,并使資源嚴(yán)格圍繞這一利益進(jìn)行配置,才能避免想入非非帶來的危險(xiǎn)。而威廉二世及其幕僚霍爾斯泰因、提爾皮茨追求的是一種純主觀的“絕對(duì)安全”目標(biāo),他們既不注重對(duì)核心利益的評(píng)估、也不考慮如何協(xié)調(diào)手段,而是以“我認(rèn)為”、“大國就應(yīng)當(dāng)”這類毫無妥協(xié)余地的口號(hào)來指導(dǎo)國防建設(shè),結(jié)果只能是“預(yù)言自證”,把沖突由可能變作現(xiàn)實(shí)。
總的來說,永遠(yuǎn)不可能出現(xiàn)不必調(diào)整就可保障長(zhǎng)久安全的政策,一種有利于國家生存的安全路線必須同時(shí)兼顧節(jié)制與靈活,就像俾斯麥所說的那樣,治國方略中永遠(yuǎn)不存在抽象的最優(yōu),因?yàn)椤罢问强赡苄缘乃囆g(shù),是可實(shí)現(xiàn)的藝術(shù)——是次優(yōu)的藝術(shù)”。(鳳凰軍事專稿 文/劉怡)
轉(zhuǎn)載請(qǐng)注明:北緯40° » 為什么鐵血宰相俾斯麥不是海軍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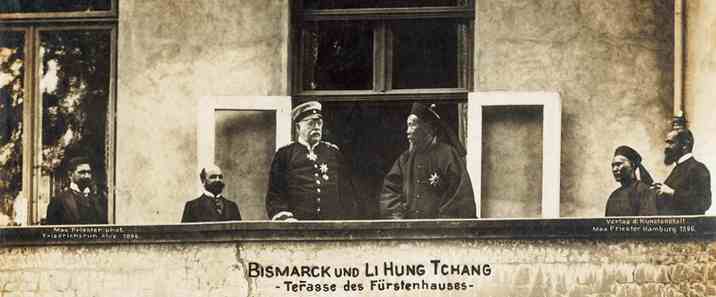



戰(zhàn)列艦.jpg&h=110&w=185&q=90&zc=1&ct=1)